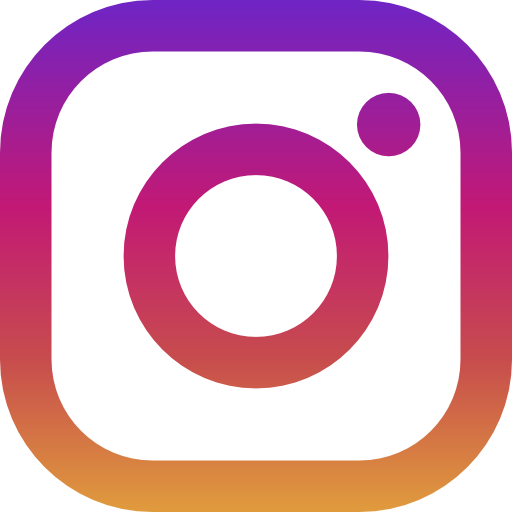FP writer, Emilie Choi’s analysis continues on the question of art labor in Hong Kong. In part 2 of her report, she asks, “what should an artists’ union do?” 據點成員蔡倩怡進一步思考藝術勞動的光景四年來沒有甚麼變動,且客觀環境越來越嚴峻。她問:「工會該如何保障藝術家?」
/…上接前文二之一
**originally published on Ming Pao Weekly #2502 (2016.10.24) 原文載於《明報週刊》第2502期
誰需要工會?
全職藝術家,卻並非等同全職創作,位置不同的藝術家處境亦不盡相同。各大藝術院校每年畢業生眾多,不少投身藝術市場熱鍋裏。然而藝術工作大多零散,年輕藝術家別無選擇,只能在藝壇謀求半職,保留創作時間。他們長期缺乏固定的勞資關係,亦欠保障,朝不保夕。年輕藝術家黃嘉瀛(KY)於是在網上發起香港藝術家工會,呼籲藝術家填表參與,工會仍在籌備階段。
| 有冤無路訴
訪問當天,KY在百呎公園召開工會的首次會議,讓會員或非會員參與討論。會議氣氛熱烈,一眾年輕藝術家圍坐一圈,爭辯工會的意義與目的,甚至如何劃分會員範圍,各人眾說紛紜。問KY成立的原意,她直道:「有冤無路訴」,「其實一直也聽過很多前輩說設立香港藝術家工會,但一直未見有人實行,所以我便來做『醜人』吧。」KY素來行徑大膽剛烈,坐言起行,工會會費十元,會章仍在草擬。
甫成立至今已有二百多位會員,她更親手自製會員卡在現場派發。盡心盡力搞工會,全因雨傘後的覺悟:「我覺得藝術家不能再獨善其身,而是確立一種群體,與合作的關係。工會希望能讓藝術家之間的資訊流動,例如一些畫廊壓榨藝術家,我們也能互相提醒,發揮團結作用。」現場的何兆南亦提到,香港過去工會意識薄弱,更毫無對藝術家工會的想像。「工會未必能實際爭取什麼,但至少對『個體戶』藝術家是一種連結。」梁御東則言,「藝術家的工作性質很多時只能單獨面對資方,而工會的重要性在於能提供參考點。」
藝術家的工作碎片化,只能孤軍作戰。不少年輕藝術家欠缺支援。好像董永康,他自2011年畢業後長期以半職工作,曾任職補習、教畫,現在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任職教學助理。而他其中一份不穩定的半職工作便是佈展。據他所言,個體戶藝術家佈展未必懂得計算合理薪酬,工傷亦無法保障。而更多例子更是畫廊只出製作費(production fee),藝術家費用(artist fee)卻欠奉,藝術家卻未必能議價,為了生計只能委曲接下。這些都是切身且實際的問題,更難言長遠的事業規劃與退休保障。
| 自己代表自己
除了藝術家之間的連結,工會亦朝向藝術架構,渴望帶入更多聲音。KY希望能讓工會發揮議題製造者的功能。「我們是否能具主導性,將一些問題帶進藝發局,將議論光譜拉闊?好像之前立法會選舉時,女同學社製作了一些問答給候選議員,了解他們對同志議題的取態。我們能否在藝發局選舉仿效,讓候選人了解我們關注的議題。」工會會議內參與討論的鄧國騫亦提到,藝術家需加強自覺。「現在香港的藝術圈發展並不成熟,許多話語權也集中在收藏家或畫廊。」因此不同藝術家的聲音更需要被聽見。
KY 強調保持藝術家的獨立自主,鼓勵「自己代表自己」。但工會講求集體意志,如何能與個體保持平衡?「工會其實是手段,比較像是一個shelter,能夠讓藝術家在安全、沒有壓力的環境下爭取權益。因為工會便是以團體責任來發聲了。」
| 藝術約章
事實上,藝發局原意以民間作本位,為藝術家發聲,卻非一個良好示範。例如其作為資源分配的機關,資助組織的藝術行政職位,薪水維持同一水平,讓藝術行政工作長期薪酬過低(underpaid)。藝術評論人梁寶山亦曾提出藝發局應做帶頭作用,建議各資助機構的職位薪水維持合理範圍。新晉藝團或藝術家,亦因缺乏資歷或無法獲取藝發局資助,循環懸殊位置。工會能否打破此等習見,扮演倡議角色,由下而上帶來切實改變?
另一點工會主張的是在論述上追求平等。KY不諱言工會要保障的是年輕藝術家——在藝術圈內欠缺話語權的一群。「過去藝術圈內太講究資歷或年齡。而加入工會的會員都視自身為勞動階級,大家是對等的。而我亦希望能同步深化討論。」因此她提到日後會舉辦更多論壇,亦計劃在12月舉辦讀書會,以及邀請不同工種的工會與各地的藝術家工會共同交流分享。
KY侃侃而談美好願景,我不禁掃興地問執行的細節問題。她坦言,工會現階段由職工盟協助於勞工署登記,距離正式成立仍有漫漫長路。但她亦言,工會的性質更像「打游擊」,保持更大的能動性。過去如程展緯亦曾提出藝術約章,保障藝術家權益。約章參考明報工會,作為拉近權力位置的工具,制衡畫廊的不公或審查之舉。
藝術家工會雖仍未實踐,改變現況的意圖卻鮮明。但最終能否在自身位置的觀照下,同樣關顧更多藝術微小環節上的勞動力,達致更具血肉骨幹的討論?
|
請病假 香港過去亦曾有藝術家提出設立藝術家工會,黃慧妍是其中一位。她提到自小關注勞工權益,因此多年前在C&G Apartment舉辦了《請病假》藝術展覽,模擬藝術團結工會,請中醫來義診。意念來自藝術家沒有「請病假」的概念。後來她亦將作品延伸作「虛擬工會」,制訂文件讓策展人及藝術家簽署。工會最後雖未正式成立,黃慧妍身為妻子與母親,亦深切體會「師奶勞動力」缺乏保障,亦難以估算。 世界各地亦有藝術家工會,如台灣的「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」,由藝術家湯皇珍與高俊弘等人於2011年成立,成功爭取政府立法,確保藝術勞動者的職業保險。英國經過三年時間,今年6月亦設立首個就視覺藝術家、應用藝術家及社會參與性藝術家組成的英國藝術家工會(Artists’ Union England),獲得英國政府頒發的自立許可。 |
勞動的真實圖像
藝術系統內部環環緊扣。藝術家、策展人、藝術行政、畫廊,各佔一席,難言直接單向的僱傭關係。正在書寫創意勞工(creative labour)議題的何建宗說到,全球資本流動讓工作性質碎片化,大家也以自僱性質(freelance)工作,形成不同的工作關係,「也自然讓剝削方式轉變了,存在互相剝削的成份。因為大家也盤算著自身的事業。」他提到,當年輕藝術家置身不同的結構,欠缺話語權,會以「自我剝削」(例如無償工作)來換取文化資本,讓剝削愈漸合理化。
當流動資本糅雜本地文化產業,便成了另一種勞動景象。梁寶山直言,西九所標誌的「大型文化藝術區」硬件,以至隨之而來的保育與活化等政策,成為「個體戶」藝術家面臨轉變的重要背景。「全球的工作也正出現”Ethno-lingustic division of labour“(語言族群的分工),包括藝術圈。許多畫廊的高層也是能操流利英語,未必成長於香港的外國精英。西九的高層位置同樣是全球招聘。整個商業藝術圈也並沒有關顧本地的藝術勞工。但他們也需要一些了解本地環境的員工在現場執行,做些實務工作。 」因此我們不難觀察到,即使政府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,仍是汱弱留強,未能惠及本地藝術勞工。
何建宗亦言,香港的公共資源趨向市場化的經濟邏輯發展。因此政府傾向資助藝團,缺乏對藝術創作者的關顧。同時重視所資助團體的持續效益。另一方面,現行政策亦以宏觀的大型基建,或教育訓練為主,勞工條例立法亦缺乏對藝術創作的考量。因此年輕藝術家難以單靠藝術創作維生,繼續發展(”art creation support art”)。
勞動方式的不同,過去我們常言的「異化」問題亦有新的轉向。梁寶山曾在研究中訪問不同藝術家,「好像其中一位,要克服空間距離,不斷飛到全球各地的藝博,要在該處現身,建立network,曾一天看到三次日出。」藝術家面對的勞動處境多不勝數,好像經常獨自困在工作室裡工作,工作與閒暇也難以分野,以至經常出席酒會建立人脈,也是一種”over-communication”。
| 工會是潤滑劑
梁寶山既是藝術家,同時長期研究藝術勞動議題,早年已積極爭取藝術家的權益。問及工會能否改善藝術家的處境?他直道:「工會是資本主義的潤滑劑。」她解釋道,工會事實上在資本主義運行不順時提供協助(如僱資糾紛),讓其能順利操作。因此需要細心思考工會的定位與效用。她談到工會的對象,以至參與的人數能否成為有效力的組織。「像美國編劇家工會,參加工會是入行的必要條件,這樣便能清晰定義”profession boundary”。」工會除了互通消息外,能否設立退休保障,或為產業政策倡議法例?這些亦是工會能擴展我們對藝術勞動的思考。
藝術圈內對工會的意見不一,梁寶山說到,「香港的藝術家並不傾向想像自己為勞工。」梁寶山說到,當代藝術過去努力擺脫市場,好像行為藝術、概念藝術等流派。「但這種趨勢實際上最能配合資本的流動(capital flow)。因為資本原來就是dematerialized及抽象的。」她直言藝術市場從過去的”You order, I produce”轉換到當下的”You produce first”,「當買家成了anonymous,藝術家也不知道其老闆是誰。彷彿多了自由與自主。」儘管藝術買賣因藝博而繞了一圈,重回收藏家主導的世代,但梁寶山說到,好像Richard Florida便曾提出”Creative Class”,浪漫化勞動想像。所謂自主是否仍深陷於當前資本主義的勞動結構,以疑幻疑真的自由來延續?
後記:Free Labour
在藝術產業裏,深埋許多隱性勞動:藝術行政、教育、保安,與藝術家成了相連的角色。他們的勞動狀態不一,卻幾近面對同樣不穩定與欠缺保障的工作特性。當藝術家同時身在藝術行政與教育崗位,藝術家工會,又能否保障更多不同的藝術職業? (二之二,全文完)
相關閱讀 Related Reading:
Emilie Choi / Realities from 2016: Today’s Relevance (1): Art Labour, the Value of Being Human 2016年飄來的記憶。今天又如何?(一)- 藝術勞動,生而為人的價值 (2020.05.30)
Linda Lai / Reading RAQS Media Collective: Manifesto 2 artists inspired: to be an artist by night? 「錄像宣言」的延伸閱讀:藝術勞工的景況:做個夜更的藝術家?(2020.04.25)